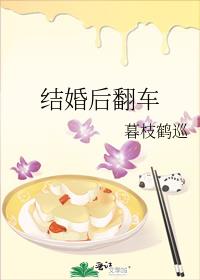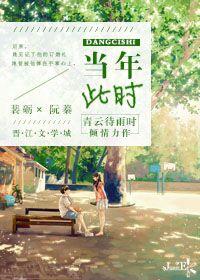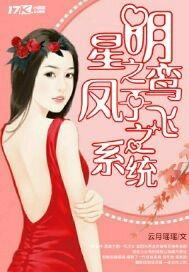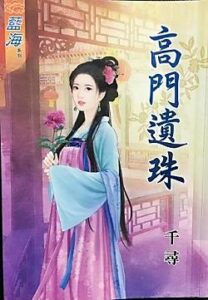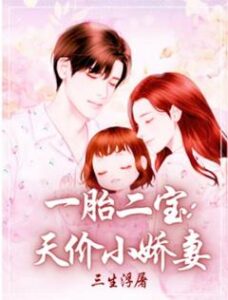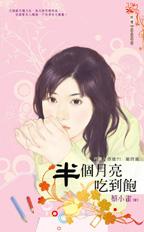野狗之家
那年冬天的尾巴是殡儀館前的隊伍。坐具和人擠在一起,不上不下。
樹下的土板結了,挾着柏油路。路中間有幾塊深斑。這裏的狗不講究。旁邊有口痰。下起小雨,這些深深淺淺就給抹勻了。冬天的雨薄而幹,不生水霧,看前邊那個小豁口,人怎麽進怎麽出、進幾個出幾個都滿清楚。前一批人放出來,隊伍往前挪,過三分鐘,又往前挪挪。照老規矩,人出來,得走罩紅光的玻璃路,做個火盆樣子去晦氣。今年緊,人一茬茬來去,也不興做樣子了。附近有知商機的,開店供人落腳。招牌說是酒店,樓層不高,客梯比貨梯吓人。
雨沒變。
畫家和攝影師一起到酒店,一前一後辦手續,一個背畫具,一個抱相機,住對面。
酒店賺錢分時間,淡季疏于打理,要麽少垃圾桶,要麽沒電水壺。畫家是沒電水壺的那個,打小害冷,無噴碼礦泉水拿了又放下,找前臺解決,路上碰見要垃圾桶的對門房客。對方挺高,毛估估一米九朝上,畫家多看兩眼,覺得手太長、不協調。過一個鐘點,畫家蹲門前張望隊伍,又看到這人貓在風口,整個人佝偻着夾了煙,因為高,更沒精神。
畫家喉嚨有點幹,摸了把口袋。攝影師聽見動靜,回過頭:“能借個火嗎?”
畫家說好,擦到第三下起火,等攝影師點上。取打火機時畫家留意借火人的手,指甲冷紫冷紫,肉刺紮堆長,關節腫脹,凍瘡加硬皮,實在是重災調色盤。手相粗,臉相更粗,三角眼一單一雙,雙眼皮翻出深深的三層,線條都硬生生的。畫家早起照鏡子,眼裏一堆紅血絲,眼袋早把卧蠶吃了,精神也不好,怕撐不住,也點了一根。雨斷片了,煙抽得人發燥,畫家掐掐喉嚨:“這隊伍沒底了。”
攝影師應了聲,說:“是慢。”
“今年不好過。”
“啊。”
“今天的?”
“嗯,一個朋友。”攝影師吐出煙圈,“謝謝。”畫家一時沒明白。攝影師擡了下煙屁股。那灰黑色有刺激性,畫家過電似的一凜。“我也來……看個朋友。”隊伍好似動了,好似沒動,畫家只管動嘴皮子,“還年輕,可惜了。”
“二十不到。”攝影師說,“很上相。”
畫家猛抽一口:“骨相也好,好得出挑。搶他做模特的有這個數。可惜走得早。”
“可惜啊。”攝影師也說,三角眼閃過一點光,又扭過頭望隊伍。畫家憑直覺感到對方說的是個問句,想想倒也該是個問句。“畫畫兒的?”
“畫了有十來年了,沒什麽名堂。”畫家舌頭打結,“你呢?”
“玩兒相機的。”攝影師把煙屁股一扔,“操,這龜孫絕了,開個破店跑小賣部買垃圾桶?”
店員拎着桶拖步子過來,小賣部門前的狗坐起來,趴回去了。等垃圾桶電水壺風波消停,上半天所剩無幾。畫家始終打不出草稿,應付着吞了半袋幹脆面,對馬桶摳喉嚨,漱完口,慢慢把指頭上的鹹味舔光,再啃指甲。
人是今年走的。托馬斯·勞倫斯畫|□□時不會想到男孩将死于十三歲,畫家從看到他時就看到了死亡。生命受到沖撞時總是會想到死。走投無路的畫家在旱季後抓到了雨季。雨季過去了。雨季不再來了。畫家對鏡子亮出發白的舌苔,全世界也是白的,開門出去,到走廊拐角的小窗臺。窗戶正對街角,紮羊角辮的小女孩趴在板凳上點手指。
畫家看了一會兒。身後喀噠一響,蹿出泡面味,沒多久腳步聲返還。兩個人蹲窗前發呆,雨又打下來,從街角折出去的矮凳終于擠進大部隊。畫家歇一口氣。攝影師說,幾點鐘的啊,進去等吧,你臉色不好。畫家搖搖頭,不說是哪個鐘點。每家人挨挨蹭蹭三五分鐘鞠躬了畢,見縫插針挑出一場死亡委實太難。
“我是聽人說,大概這天。”畫家剛剛倒空了胃,說話糊裏糊塗,“致哀輪不上我。我認識他,一天不到,就認識這麽久。”
“聊聊?”
“聊聊。”
畫家小時候有個夢想,找最美的畫布,畫最美的畫。找到之前,落下的每一筆、擦去的每一痕都是在醞釀相逢。畫家獨自在黑色繪畫中朝聖,等待日出。“我等到了。”畫家嘆息說。他們在畫室門口遇見。那年輕人在圈子裏頗具名氣。他很美。畫家遠遠望見他的背影,靈感偾發,手沉得提不起畫筆。不要轉身。別被看見。畫家苦苦祈禱,但腳步失控向前。年輕人轉身。畫家看到他。
“他很美。”畫家嘆息說。廊道裏雨色單薄,瑩綠安全燈魅影般蕩過,大衣挂着醉人的煙味,不知道該怪誰。攝影師點頭,漫不經心踩着影子:“他很美。”
語言是貧血的藝術。如果要描述他,除了“美”,其他全不恰适。“漂亮”“美麗”“絕美”都多餘,那種美不拘于屬性,超越程度。攝影師結識他之前沉溺于小衆藝術,偶像是喬·彼得·維特金和黛安·阿勃斯。維特金的鏡頭裏,美女和腐屍共舞,一個人的兩半頭顱親吻自己,生死美醜被一視同仁。阿勃斯直刺世界的黴斑,用冷靜的筆寫心上的破洞。攝影師膜拜這種矛盾又公平的鏡頭語言。買下第一臺相機後,攝影師在筆記本上寫道:“捕捉人性,把人性賦予一切非人性。”
那種美是人性的,因為它可被任何人欣賞;也是非人的,過于圓滿,沒有殘缺。畫家顫抖着邀請他走進工作室。工作室有天窗,畫家在那裏布置了漫射屏和消色差燈泡。光線柔和而勻稱。畫家打開劇院聚光燈,調正高度和光束寬窄。畫布無比潔淨。畫家暈眩地望着他。他拿着飽滿的蘋果,咬了一口。甜美的汁水在畫家耳邊迸開。
攝影師把蘋果放在凍死的鳥旁邊。凍瘡從那年冬天起上門造訪,手指僵麻,難得等到對的時機,想要捕捉,往往錯過。攝影師在鄉下有套別墅,一部分用作暗房,一部分挂舊的新的照片。每年的三分之二,攝影師都待在那裏,過了祖母祭日再回市區公寓住。那天,攝影師在門前撿到這只死鳥時,無名指上的一塊凍瘡開始結痂,新的是嫩紅色。剛結束晨跑的攝影師忽然感到寒冷。蘋果還挂着水珠,攝影師放回照相機,把鳥和蘋果扔了。晚些時候,攝影師驅車回市區,和同行朋友約飯泡吧。朋友帶了人。成年了嗎,攝影師說。年輕人微笑,酒杯讓笑變得朦胧。攝影師把濕熱的手貼在嘴唇上。我要拍你。
我想畫你。沒有相稱的畫布。畫家翻遍工作室,又翻遍記憶。沒有合格的畫布。年輕人吃着蘋果,畫家看着他的手。手指、手腕、小臂、頭頸、腳踝,畫家跳過衣料看到畫布的一角。燈暗了。畫家細細撫摸衣料裏側,從溫變涼,從邊角到全部。他銜着青黑的果柄,顏色孤零零的。畫家想到豐腴的酒神。脫衣服,畫家幹巴巴地說。聽起來像命令。布料散落。畫家看見了最美的畫布。
攝影師把他的衣服脫了。這具身體很年輕,也很美。攝影師讓他躺在岩石上,白浪拍打他的腳踝。遠方飛來海鷗,影子落在沙粒上。
這張照片以 16×20 英寸進入畫框,展出時,攝影師堅持要用海藍的背景牆。另外有一幅,尺寸稍小一些,被相框束起來,方便帶到天涯海角。攝影師把相框放在桌上。門喀噠關上,電磁卡叫醒廊燈,照片裏海浪複活,波紋滾上珍珠色趾甲。畫家背光站着,後背僵硬地貼着門。攝影師珍愛黑白照片,身邊總帶着最喜歡的幾張。賓館房間貼着黑與白,被布置成臨時靈堂。有幾張被做成海報,影調大多偏暗。正中是淡灰的胴體,影調範圍很小,淡得輕飄飄。畫家眯起眼,覺得那像掉進黑棺材的伊甸園。
“做了點遮擋,用蒙版降低反差。”攝影師指着岩石縫隙。模特模仿着波提切利的維納斯,小腿在廣角鏡頭裏變形。攝影師沿模特小腿上劃,來到天空:“這裏原來更亮一些。”
“挺有意思的。”
“嗯?”
“在攝影剛誕生的時代,很多人說繪畫死了。今天,很多人喜歡用照片模仿畫作。”
“大衛·霍克尼說攝影正在死亡。”攝影師說,畫家夢游似的搖到照片前面。畫家鼻頭毛孔很粗,兩邊有小雀斑。
“都會死的。”畫家看着照片說。
雨在屋外滴滴答答,偶爾傳來一兩聲狗叫。屋裏的人知道今天有一場葬禮,在某個時刻,雨或停或不停,但腳只是沉沉地粘在原地。畫家的速寫本裏有實際的他,有想象的他,素材豐碩,但無法建構他的死亡。攝影師拍過屍體,為死者趕到這裏,但設計靈堂已經耗空力氣。他死了,像個模糊的印象;是個明确的轉折,斷骨戳破皮一樣。他們追着印象跑出很遠,死亡驀地打下來,不知道往哪裏跑了。
畫家在床角坐下來,來來回回撥弄手機裏的相片。有一串照片,連着大概二十張,拍的是同一幅畫。主角是那個很美的奴隸,他頂上是黑雲與雷電,腳下是灰埃與岩漿。畫家把畫給攝影師看。“兩三年前畫的,得過一個小獎。”之後兩三年畫家沒有作品。
年輕的模特跪在地上,全身赤|裸。畫家将他雙手綁到背後,挪回畫架,總覺得缺了東西。在指令下,模特伸直頸部,放松胯部,松松張開腿,膝蓋着地面。畫家站在他身後修正軀幹上的彩繪,再回頭看效果,還差了一些,說不清楚。然後畫家脫了衣服,狗爬般跪在那裏,親身演繹一個被夾在希望與絕望間的奴隸。奴隸低着脊梁,卻要拼命擡頭。畫布上已有白顏料劈出的閃電,窗外天暗了。門被撞開。
攝影師摔上門。門裏是僵直的祖母,嘴巴張開,嘴唇向那個深深的黑洞收縮。老門板不厚實,争吵漏了風。攝影師蹲在門板外。中年人把財産談妥了,這裏沒有攝影師的事。有個人突然說,媽的底片呢,堆着不好。屋裏靜了一會兒。處理了吧。幾個聲音七零八落,內容整整齊齊。攝影師眨動幹澀的眼睛,背上雙肩包離開。那年柯達膠卷停産。祖母拍照拍了四十多年。攝影師拍了十幾年,沒用過數碼相機。
畫家學畫學了十幾年,起初是學國畫,因為父親認為有氣質。在轉投西方畫幾年後的某個夏天,父親拍開畫室的門,瞪着地上一個裸人和一個裸人,臉紅轉青轉紅,鼻孔重重噴氣。他提住畫家的淡頭發,搧了一個大耳光。畫家垂着頭。搞藝術!你搞藝術!啪!搞!啪啪!不檢點!
“得過一個小獎。”畫家笑笑,啃指甲,“不少人私底下叫它‘強|奸’。”
“搞藝術就是強|奸。”是強|奸,是狗咬死狼,一切不安本分的反常。攝影師往水壺裏灌水,倒出來。燒水壺內積着水垢,外層塗漆剝落,露出慘灰的不鏽鋼。“強|奸生活。”
用熱水沖了茶,沒滋沒味的。畫家才解開滑雪衫,丢椅背上挂着。高領毛衣讓畫家更接近于直線。攝影師坐或站背都彎,兩條長手把脊柱往下拽。兩個人坐一塊兒,個頭差得不多。牆面一半是照片,隐隐有倒塌的趨勢。畫家不知不覺從床腳躲到床頭,手摸着被單,一個煙燙的洞。枕套泛着黃,軟塌塌,像隔泡爛的沒包好的隔夜餃子,污漬內餡般翻出來。再過去些,床板和枕頭卡着一只沒用過的安全套。挺應景的。
“我以前學國畫,畫山水,仕女,都很雅致,不大像人。”國畫不畫強|奸,畫家說,“我想畫人。”
夢想大多被拿來摔打。老房子裏,冰箱門是發黃的、無灰的白,上面貼着兩張紙,一張必做事項一到九,一張家門規矩二三十,筆跡橫平豎直,像油亮的拶子。畫家小時候坐冰箱下面,鉛筆橫豎各劃兩下,小指頭把鉛灰抹勻,不當心蹭髒領子,晚上挨一頓罵。
畫家的父親有正經的職業,人也正經,食不言寝不語,七點切新聞頻道,最大愛好是“不玩物喪志”,次一級愛好是寫大字。母親的事業是支持父親。畫家不喜歡父親的字,以為線條應該有活氣。父親不喜歡畫家曲背,畫家的背現在是一條僵屍似的直線。畫家割離那個家已經很久了,骨頭還保留着父親的形狀。
線條鈎住視線,視線別無選擇。很長一段時間裏,攝影師只追逐線條。日落後,點狀光被沖淡,包豪斯建築的利落線條在光影中變形。在不适合攝影的午後,山巒仿佛被燒灼,赤青黃綠分割岡岩,曲線與直線交結,筆筆出天然。一張照片裏,攝影師讓木雕挂件枕在掌心上,調正光圈,木紋放大後是扭曲的吶喊。攝影師用暖調相紙擴印它。有人問起邊緣的白刺。攝影師沒告訴任何人那只是死皮,被剝過但沒被剝幹淨的。說出來當然更好,木雕的死亡、皮的死亡,主旨鮮明。木雕不會呼吸,攝影師不喜歡往下聯想,但克制不住把兩件東西放在一起。死皮也是美的,白白淺淺,有的像蚜蟲有的像雲邊,撕一下,線條介于可控與不可控之間,讓人着迷。
父母離異前些天,攝影師在寂靜的床上撕死皮,父母用優雅的詞彙撕咬這個家。死皮撕光了,攝影師撕掉全家福。這相當考驗眼力和技術,得把兩顆頭和一邊肩膀拽開,得把兩條手臂從腰間剔除。正中的女孩腰部有別致的镂空圖案。照片裏的人不需要肺。照片外的攝影師難以呼吸,轉着剪刀,去掉那兩條手臂蓋着的地方,把自己剪成怪物。單純的線條和形狀竟然也可以要死要活。攝影師拎着小怪物背上背包,乘很久的公交到郊區。祖母整理閣樓,攝影師專注地閱讀老照片,看書的樣子被祖母放在了這本相冊的末一頁。後來攝影師愛上維特金,是對那兩條手臂下的肉塊的紀念。
“我也喜歡線條。”畫家說。奴隸頹敗的背被土地和繩索束縛,頸部的線比雄鷹昂揚,很有力度。畫家捧起腫大的關節,在這雙手裏找那一幅真正的畫。它像節疤,粗野、冰冷、有力度。畫家的指腹在臂彎停住了。黑白照片把房間染灰,兩個人腳對腳,對視着,像兩只淋泥漿雨的青蛙。
畫家在速寫本上畫下線條,畫彎曲的脊柱和背間的凹陷。攝影師躺在床上擺弄照相機,長發裏掉出兩根白絲。兩條消息同時發到兩只手機,一長串字,依稀夾着一個确定的鐘點,都沒人管。攝影師站到照片下,用 24mm 鏡頭對準床上的女人。這不是理想的肖像鏡頭。由于透視畸變,鼻頭放大,就像兩個稚嫩的腫瘤。女人壓下背,擡起頭,黑眼圈把眼神塗得迷離不清。攝影師這樣把女人拍下來。畫家合上速寫本,頭又低下去。黑與白的照片不知道什麽時候撤下了。
外面雨停了。街口留下一只濕板凳。狗過去嗅了嗅,被小賣部的五花肉香誘走。再過去幾十米,一行人走過罩紅光的路,慘白的臉滲出笑。